“如果不能演奏出完美的音乐克拉默,我们就会被送去毒气室。”女指挥家罗斯用如此毛骨悚然的语汇“激励”、“恐吓”着自己乐团的成员。罗斯只是个传声筒,乐团身处的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才是恐吓真正的发声者。
这支身世特殊,维持了一年多的乐团,就是“奥斯威辛女子交响乐团”
当时在各大纳粹集中营中都相继成立了交响乐团,奥斯威辛男子集中营也早在1941 年建立了自己的交响乐团。出于不甘落于人后的目的,残暴的音乐爱好者、奥斯威辛女子集中营的临时主管曼达尔自1943 年春开始筹建乐团。扎亚科夫斯卡这位相传是柴可夫斯基家族后裔的波兰音乐家成为了乐团的第一任指挥。
乐团建立伊始,吉他,曼陀林和一些打击乐器是乐团仅有的家当。由于乐器和乐谱的缺乏,最初乐团仅仅排练演奏一些德国进行曲和波兰民歌。这样的曲目安排也是出于纳粹对乐团的功用期许。
当时乐团最主要的工作便是在集中营门口,为出工和返工的难友演奏;在新的一批难友乘坐死亡专列到达营房时,安抚他们焦虑紧张的心情;也在难友前往毒气室的路上为他们演奏——仿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冲淋。
1943年8月,阿尔玛·罗斯取代扎亚科夫斯卡接手了乐团。这位在当时欧洲已经小有名气的小提琴家有着显赫的家世——她的丈夫是捷克传奇小提琴家普利霍达,父亲罗斯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罗斯四重奏的发起人,母亲马勒则是大作曲家马勒的妹妹。
1932年,阿尔玛·罗斯组建了维也纳华尔兹女子乐团,率团在欧洲进行了广受欢迎的巡演。1938年,乐团被纳粹当局勒令解散。翌年她在弗莱舍的帮助下,和父亲一起逃到了伦敦。安顿好父亲后,她又旋即离开了英伦三岛,重返大陆,在荷兰进行秘密室内乐音乐会,从而也开启了她的“死亡之旅”。1942年,几经躲避逃亡她还是在法国被抓获,次年被送往了奥斯威辛。
起初,乐团的团员大多是没有受过太多专业训练的业余非犹太裔乐手,罗斯甫一接手,就开始招募专业的犹太裔乐手。德国女大提琴家、战后英国室内乐团的创始人之一拉斯克-沃尔夫费什刚入营区,惊魂未定,就诚惶诚恐地在罗斯面前试奏了博凯里尼大提琴协奏曲的慢板乐章,舒伯特的《军队进行曲》。
另一位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的法国香颂歌手菲奈龙,刚踏入监室,就听到了看守在大喊克拉默:“谁会唱歌,谁会钢琴?”虽然当时她身体极度虚弱与疲惫,但她还是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来到罗斯面前演唱了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选段。随后她立即被转入了专属乐团团员的监室。
很快,这支混编乐团在演奏技艺上突飞猛进。在她们的保留曲目中,已经出现了贝多芬,格里格,舒伯特,肖邦,门德尔松的作品。
被收编入队的大提琴家Anita Lasker - Wallfisch,“在集中营演奏大提琴救了我的命”
乐团曲目的拓展,演奏的精进,也使他们收到了集中营高层的邀请。他们定期会在党卫军的派对上演出,甚至为监狱管理人员单独演奏。菲奈龙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访问时,讲述了她们为监狱长克拉默演奏的故事。
“当我们演奏舒曼的《梦幻曲》时,监狱长克拉默哭了。他将超过24000 人送进了毒气室。当他工作干累的时候,会到我们这儿来,聆听我们演奏音乐。”
“这些纳粹军官让人难以理解,他们能无情地枪毙和杀害他人,把别人送进毒气室。但当他们做完这一切,音乐响起时,又会变得如此敏感。”这一叙述不免又让我们联想起电影《钢琴家》中那个著名的片段。
因为纳粹军人们的喜爱,他们得到了更多的特权,他们居住环境舒适,有更好的食物,不会受到生命的威胁,甚至掌管了集中营的一些生杀大权,凡是被交响乐团吸收的人,都可以免去死亡。
1944年4月2日,在党卫军的私人派对上,阿尔玛·罗斯进行了在集中营里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出后不久便感剧烈头痛、腹痛,两日之后在医院中离奇死亡。虽然她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过相较于投毒陷害这个传说,一般还是认为她死于食物中毒或者突如其来的某种传染病。
离奇的死亡也许也是这位音乐传奇最合适的终点。鉴于她在集中营中特殊地位,党卫军为她举办了颇为隆重的悼念仪式——他们为她的灵柩穿上了素朴的白衣,四周布置了鲜花。这或许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在集中营里,党卫军向犹太死者致敬。
那些年我们一起玩过的《大海战II》现在又出正统续作《大海战:烈焰与重生》,目前火爆封测中,封测报名网址: nf2.kupai.me 加入我们一起重温那逝去的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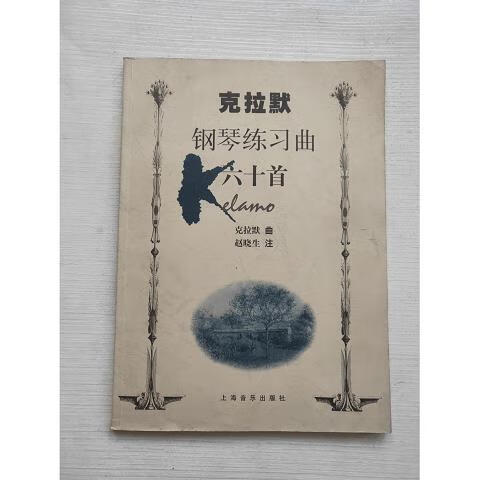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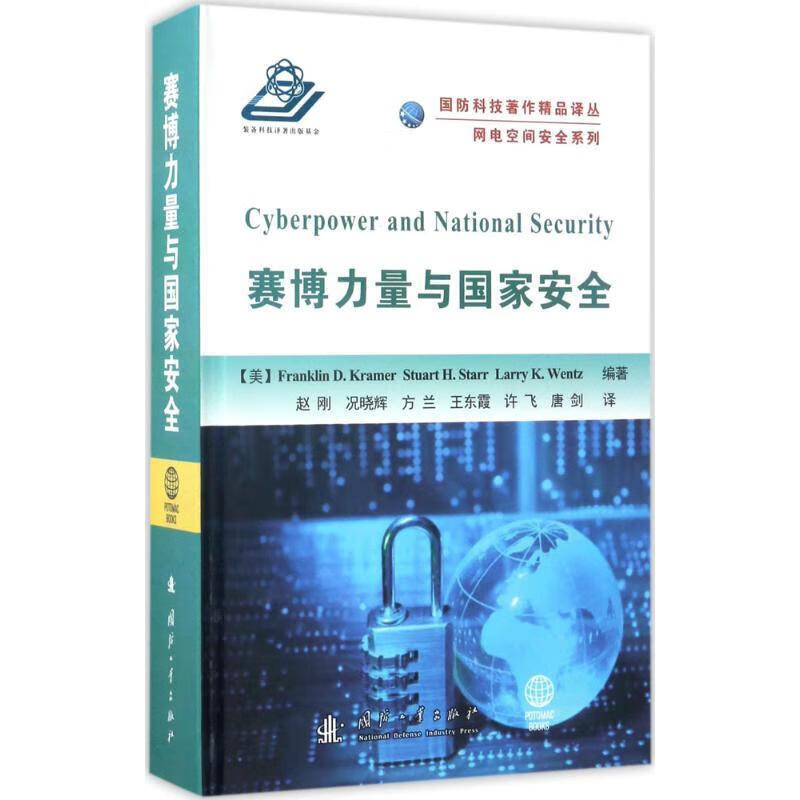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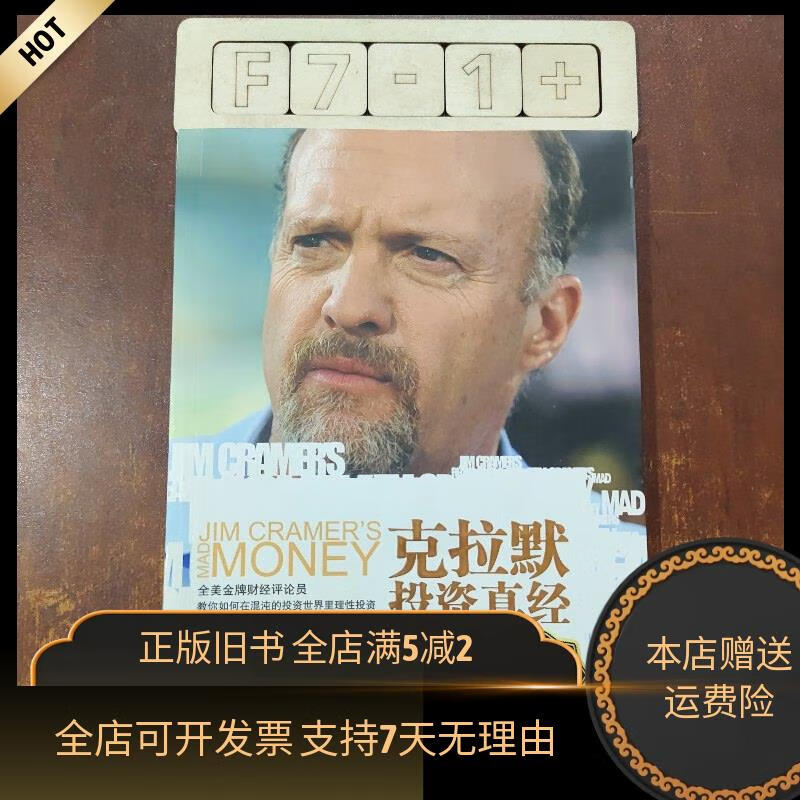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